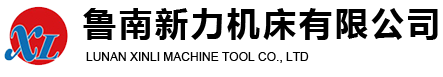既然“遍地都是”,科學(xué)家為何還要找三年
中國科學(xué)報2025-05-12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也許你經(jīng)常在一些植物新種發(fā)表的新聞下,看到這樣的評論:“有什么稀奇的,我家屋后都是”“植物學(xué)家大驚小怪”“這有什么用”……近日,一則關(guān)于“西南大學(xué)教授發(fā)現(xiàn)異鱗石山棕”的視頻報道,也引來諸如此類的質(zhì)疑,甚至摻雜著對研究人員科學(xué)素養(yǎng)的嘲諷。
“外行人看熱鬧,內(nèi)行人看門道。”一些網(wǎng)友眼中“相似”或“一樣”的植物,從植物分類專業(yè)角度講,其實“大有不同”。況且植物新種的認定和發(fā)表,需要經(jīng)過嚴謹?shù)目茖W(xué)考察和反復(fù)論證,并非隨意而為。
而當(dāng)網(wǎng)友調(diào)侃“這有什么稀奇”時,他們不知道其蘊含的獨特基因庫里可能藏著解決人類重大問題的鑰匙;當(dāng)人們嘲笑植物學(xué)家“大驚小怪”時,他們不懂生物多樣性監(jiān)測對生態(tài)安全的意義。
科學(xué)教育不應(yīng)止于知識傳授,更要培養(yǎng)對專業(yè)主義的敬畏之心。
科學(xué)研究不允許半點取巧
2017年,西南大學(xué)教授李先源在武陵山大裂谷考察時,注意到類似石山棕屬植物。“該屬植物多分布于熱帶及南亞熱帶,怎么會出現(xiàn)在北亞熱帶崖壁上?”
此后一年,李先源頻繁赴當(dāng)?shù)赜^測,以便采集該植物的花和果實。他后又赴該屬主要分布區(qū)——廣西采集標本比對,研究發(fā)現(xiàn)武陵山樣本在葉鞘纖維及葉背鱗片的形態(tài)上存在顯著獨特性。
沿烏江流域補充調(diào)查時,團隊又發(fā)現(xiàn)了該植物的多個居群。經(jīng)形態(tài)學(xué)與分子證據(jù)反復(fù)驗證,李先源團隊于2019年將這一新種命名為“異鱗石山棕”并正式發(fā)表。
面對網(wǎng)絡(luò)上掀起的這場“無妄之災(zāi)”,從事植物分類學(xué)研究近40年的李先源雖感無奈,但也表示“看得開”。他強調(diào),新種認定都得經(jīng)過長期野外追蹤與多維度科學(xué)驗證,“科學(xué)研究怎能允許半點取巧?”
中國科學(xué)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胡君對此也深有體會。他從事植被與植物多樣性考察已有10余年,近日發(fā)表了一個歷經(jīng)3年才認定的新種“成都衛(wèi)矛”。
最開始,胡君團隊在成都龍泉山拍攝到這株衛(wèi)矛科植物后,先將其定位到衛(wèi)矛科內(nèi)相似種冬青溝瓣和刺葉溝瓣。前者僅存3份110年前英國植物學(xué)家威爾遜采集的果期標本,后者標本較少,花的描述不完整,且缺少影像資料。
于是,胡君便將信息分享給團隊成員,并提醒大家在野外考察時多加注意。沒過多久,團隊采集到與文獻描述高度吻合的刺葉溝瓣及冬青溝瓣標本。經(jīng)形態(tài)學(xué)比對和分子測序分析后,胡君確定龍泉山采集的衛(wèi)矛科植物與已知的兩個近似種不同。
因此,在2022年至2024年,胡君又多次前往龍泉山,在不同時期對疑似新種進行形態(tài)觀測和記錄。經(jīng)過形態(tài)特征的進一步比對,他才確認其為衛(wèi)矛科植物新種。
科學(xué)研究有“偶然”,有的新種就是研究者在考察中“偶遇”后才開始關(guān)注的。不過,“偶然”中有“必然”。長期反復(fù)仔細的考證,就是研究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必然”。
然而在短視頻時代,碎片化敘事將跨越數(shù)年的標本比對、分子測序和形態(tài)學(xué)論證,壓縮成30秒“偶遇得真理”的流量爆款,容易給人造成“得來全不費工夫”的錯覺,忽視了科研背后不為人知的跋涉。
“看到”和“發(fā)現(xiàn)”是兩碼事
在成都衛(wèi)矛的認定過程中,聽說某地發(fā)現(xiàn)了相似種刺葉溝瓣后,胡君就到相應(yīng)點位多次蹲守花期和果期,以獲取該物種完整的形態(tài)特征。因為植物的花、果實和種子結(jié)構(gòu)(繁殖器官)在進化中相對保守、變異較小、特異性強,是區(qū)分物種的核心依據(jù)。
他表示,同一科甚至同一屬的植物畢竟是“親戚”,但只是看起來像。“花瓣數(shù)量、果實紋理、葉片厚度和葉脈走向……都是不可忽視的細節(jié)。”
但公眾常將植物分類簡化為通過花瓣數(shù)量、葉形區(qū)分物種,對背后復(fù)雜的形態(tài)學(xué)分析體系缺乏認識,同時對植物分類學(xué)的理解也多停留在標本采集和制作階段,未觸及其核心邏輯。
更有甚者對自己未知的領(lǐng)域少了敬畏之心,所以出言便是“我家屋后都是”“沒啥稀奇的,有什么用”。
“暫不說這位網(wǎng)友家屋后長的是不是報道所提的新種,我們從專業(yè)角度講,‘看到’和‘發(fā)現(xiàn)’本就是兩碼事。”胡君解釋,很多植物在正式被認定前,很可能早就被當(dāng)?shù)厝耸熘鶕?jù)形態(tài)取了名字,甚至還被當(dāng)柴燒或者入藥。但科學(xué)研究所講的“發(fā)現(xiàn)”,始終遵循著一定的邏輯和流程,以及嚴謹、審慎的原則。
胡君提到,以前關(guān)于植物“活化石”水杉發(fā)現(xiàn)者的認定,曾引起業(yè)內(nèi)的激烈討論。“這件事雖然是關(guān)于‘發(fā)現(xiàn)者’的爭議,但也透露出一個共識——新物種的‘發(fā)現(xiàn)’,是采集了標本,又加以研究確定為新東西,并正式發(fā)表才算數(shù)。”
更為重要的是,普通人的“看到”只是熟悉或者欣賞,而植物學(xué)家的“發(fā)現(xiàn)”是一項必要且基本的科研步驟,目的是不斷認識我們所處環(huán)境的生物多樣性,了解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構(gòu)成和功能,更好地保護和管理自然資源。
一些未知全貌便拋出“無用論”的網(wǎng)民,在興致盎然地打開手機、利用拍圖識植物的軟件時,恐怕也不會想到,這快捷工具依賴的就是數(shù)百年來植物分類學(xué)家“發(fā)現(xiàn)”的成果。
“冷門”背后的積累和堅持
和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估值”領(lǐng)域比起來,植物分類學(xué)的確顯得“冷門”“無用”。前者常能帶來立竿見影的成果,讓人直觀感受到生活的變化,而后者少有直接商業(yè)轉(zhuǎn)化路徑。
況且媒體傾向于報道“能解決現(xiàn)實問題”、更吸引眼球的應(yīng)用成果,而對基礎(chǔ)科學(xué)進展和深遠意義常常簡化或弱化。
這種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使得公眾對植物分類學(xué)這類需要長期積累的學(xué)科陷入認知誤區(qū)。成長于即時反饋的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的網(wǎng)民,既難以理解分類學(xué)家數(shù)年追蹤一個物種的執(zhí)著,也總是忽略“沒有根系的深扎,怎有果實的豐碩”這一道理。
胡君說,植物調(diào)查和分類工作,考驗著從業(yè)人員的體力、耐力以及悟性。
“我們既要走進深山峽谷高原,去植物生長的第一線,也要甘于寂寞和枯燥,在大量文獻資料里反復(fù)斟酌。”胡君認為,這項工作需要傾注熱愛才能堅持,因為做分類研究會面臨申請不到好項目、遲遲發(fā)不了文章的困境。
這個過程中,相關(guān)學(xué)者的自我積累很重要。除了植物學(xué)基本知識,他們還得建立起地理學(xué)、生態(tài)學(xué)和分子生物學(xué)復(fù)雜的知識體系。語言方面,不僅要識得英文,還得學(xué)點拉丁語,因為植物學(xué)名必須用拉丁文進行書寫。
“甚至要了解科考所在地的民俗,以便和當(dāng)?shù)乩习傩沾蚪坏馈!焙硎荆谝巴猓瓶紙F隊的力量畢竟有限,有時候就得“走群眾路線”,讓熟悉周圍環(huán)境的農(nóng)戶、牧民、護林員等帶路,說不定能獲取不少有效的線索。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看看一些‘吃瓜群眾’的言論,會發(fā)現(xiàn)不是完全無道理。”胡君說,要“正確看待”這些信息。
就像成都衛(wèi)矛,其分布的海拔高度只有800米左右,附近農(nóng)戶上下山途中估計都見過。網(wǎng)友說他家屋后有成都衛(wèi)矛,說不定還真有。
也許,科研人員可以主動回應(yīng):“你說后院到處都是,那我們就去看看,到底是不是。”(記者楊晨)
| 版權(quán)聲明: 1.依據(jù)《服務(wù)條款》,本網(wǎng)頁發(fā)布的原創(chuàng)作品,版權(quán)歸發(fā)布者(即注冊用戶)所有;本網(wǎng)頁發(fā)布的轉(zhuǎn)載作品,由發(fā)布者按照互聯(lián)網(wǎng)精神進行分享,遵守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無商業(yè)獲利行為,無版權(quán)糾紛。 2.本網(wǎng)頁是第三方信息存儲空間,阿酷公司是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服務(wù)對象為注冊用戶。該項服務(wù)免費,阿酷公司不向注冊用戶收取任何費用。 名稱:阿酷(北京)科技發(fā)展有限公司 聯(lián)系人:李女士,QQ468780427 網(wǎng)絡(luò)地址:www.arkoo.com 3.本網(wǎng)頁參與各方的所有行為,完全遵守《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條例》。如有侵權(quán)行為,請權(quán)利人通知阿酷公司,阿酷公司將根據(jù)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guī)定刪除侵權(quán)作品。 |
 m.quanpro.cn
m.quanpr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