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自然不可棄自然而去
陶思明

《生物多樣性公約》確立了就地保護的主體地位,“序言”部分即開宗明義說:“注意到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基本要求,是就地保護生態系統和自然生境,維持恢復物種在其自然生境中有生存力的群體。”而遷地保護僅作為“輔助就地保護措施”提出。我國《環境科學大辭典》在“就地保護”詞條中也有對“遷地保護”的定位,即“遷地保護可以作為其補充手段。”但從近一個時期的有關文件和宣傳看,遷地保護和就地保護已經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了,不知道以后怎么個發展方向。
最近,通過網上搜索試圖更多了解遷地保護的概念和定義時,在百度百科上意外看到佐證其“遷地保護”詞條內容來源的應用案例:“遷地保護——拯救白鱀豚的唯一選擇”(原載于2002年7月15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記者報道,圖片和內容附后)。從報道看,20年前長江還棲息白鱀豚近百頭,對一個大型物種來說也算可觀,但后來都不見了蹤影,甚為惋惜。同時感到提煉和反映當時保護觀點而來的報道標題,意涵太絕對化了,白鱀豚明明在長江里,保護卻不依賴于長江,要其離開現狀分布區遷到別處去才能保護,而且還具唯一性。這成什么邏輯,長江里還有那么多物種都需要保護,難道都要一一遷出不可,母親河是有豐富生命實體的,也不允許掏空呢。由此可知,以此佐證的遷地保護詞條,恐怕也難免片面。
很多野生動物都具備生境的選擇和決策能力,在哪兒生活是對環境的長期適應,不生活在哪兒意味著那里不具備條件。一些野生動物長期固守既有家園,人們總結其特點是“寧要山,不要命”,說明對適應了的環境條件的剛性需要。而白鱀豚在距今2500萬年前進入長江生存進化,能堅持數千萬年時間不改初衷,即便隨著人類社會發展涉長江經濟活動越來越多也不離不棄,演化為人們心目中的“長江女神”,為什么?簡單說還不是因為長江在中國江河中水量最大,江水最深,水生生物最豐富,氣候也溫和等,長江的波瀾壯闊對白鱀豚有著風景這邊獨好的吸引力,白鱀豚對長江的烙印之深也使其無法離開長江了。
那我們不在長江里保護白鱀豚,想遷到哪兒去才算保護?有更好的去處它不是早就去了,還用等到現在。如果連這點靈性都沒有,怎么稱得上是“女神”級的野生動物呢!而且長江也不是干涸消失沒有了或發生其他重大變故,只是對白鱀豚等水生生物有威脅的人類活動比過去多了而已。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本意,就是通過管控減免人類活動威脅解決問題的,現在長江“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說法,是對保護最精準的解釋。也就是以問題為導向給白鱀豚等長江水生生物減壓減負,盡可能去除人的過多干擾,有效恢復生境的自然性,否則還能怎么保護,又怎么受經濟利益掣肘使保護難上加難。不過再難也要保護,就算沒有白鱀豚,長江其他眾多水生生物多樣性也同樣要保護,怎么能說遷地保護是拯救白鱀豚的唯一選擇,難道它就不能選擇就地獲得保護,這太不可思議了。
先不說別的,要遷出保護就要找到和捕捉白鱀豚。長江體量多大,白鱀豚何其聰明,怎能不自我堅持而心甘情愿逆來順受、束手就擒,從過去捕捉工作部署和操作描述看,尋找和捕捉白鱀豚的過程可以說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如電動船、沖鋒舟驅趕,白鱀豚沖破三層捕網而逃逸使捕捉失敗等,這該是什么勁頭,對出水呼吸的哺乳動物又意味著什么?就算捕捉到活體也異地養上了,但其在原生生態系統不是單一個體存在,而是和生命共同體又著千絲萬緒的聯系,更習慣了獨一無二的長江水文特征等,再好的遷地保護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也就只能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暫行茍且偷生罷了。還有生態系統服務,遷出后就只有個體價值,連帶著簡化了原生態系統結構和服務產出,影響是深刻的。
有人說科學研究不能預設結論,看來試圖以人為力代替自然力的遷地保護,也不能預設結論。否則在沒有驗證過的路徑上朝著心定目標一路高歌猛進,成功了當然很好,但失敗了不僅竹籃打水一場空,最怕連自然本體都搞沒有了,社會和生態代價太大。這篇被引用驗證詞條的報道,一開始就說:“中國水生生物學家日前調查提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白鱀豚總數已不足100頭,如不采取特殊措施加緊搶救,有可能20年之內滅絕,應盡快遷地保護白鱀豚。”實際上白鱀豚就是從遷地保護起步的,一路強化,可也沒有保護住。
自然是復雜的,生命特別是可以離地活動、有習性養成和豐富情感的野生動物,其棲息地選擇和生活史更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生物多樣性公約》有關就地保護是保護生物多樣性基本要求的共識,是匯聚全人類聰明才智和經驗教訓而來的。我們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劃設生態保護紅線,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流化,其實都是在做就地保護的工作。但從現實看,就地保護的地位還需要再提升、再鞏固,要從遷地保護白鱀豚是唯一選擇以及其他同樣的理論和實踐中汲取教訓,模范踐行“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生態文明理念,除非有利用需要,能就地保護的最好不要遷地保護。自然保護中也喜好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甚至棄自然而去保護自然,這在理論上說不通,實踐上是有害的。
遷地保護不是不能搞,有高昂進取精神也是可貴的,但最好審慎以待,根據不同目的和物種,且行且看必要性、可能性和實際效果。野外有自然分布、遷地保護也是自野外獲取種源的物種,無論如何要以就地保護為優先選擇,遷地保護有興趣試驗一下也未嘗不可,但看著不行就馬上以仁愛之心回到自然中來。按一般說法,即便遷地保護成功了,也還要回到原生分布區,與其如此還不如直接就地保護算了,何必遷出遷入、家野互變不斷折磨心愛的保護對象。依托自然保護自然符合自然期待,不會有大錯,自然和人一樣不到最后一刻絕不會尋死不活放棄自我,以致同樣人類活動影響強度下,那些大多行自生自滅的野生生物,反而都活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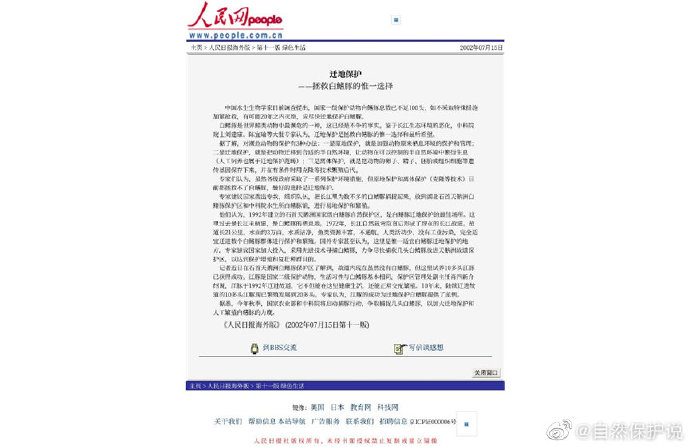
遷地保護——拯救白鰭豚的唯一選擇
中國水生生物學家日前調查提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白鰭豚總數已不足100頭,如不采取特殊措施加緊搶救,有可能20年之內滅絕,應盡快遷地保護白鰭豚。
白鰭豚是世界鯨類動物中最瀕危的一種,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鑒于長江生態環境的惡化,中科院院士劉建康、陳宜瑜等大批專家認為,遷地保護是拯救白鰭豚的惟一選擇和最后希望。
據了解,對瀕危動物的保護有3種辦法:一是原地保護,就是加強動物原來棲息環境的保護和管理;二是遷地保護,就是把動物遷移到合適的半自然環境,讓動物在可以控制的半自然環境中繁衍生息(人工飼養也屬于遷地保護范疇);三是離體保護,就是把動物的卵子、精子、胚胎或組織細胞等遺傳基因保存下來,并在有條件時用克隆等技術繁殖后代。
專家們認為,雖然各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護環境措施,但原地保護和離體保護(克隆等技術)目前都拯救不了白鰭豚,最好的選擇是遷地保護。
專家建議國家撥出專款,組織隊伍,把長江里為數不多的白鰭豚捕捉起來,放到湖北石首天鵝洲白鰭豚保護區和中科院水生所白鰭豚館,進行易地保護和繁殖。
他們認為,1992年建立的石首天鵝洲國家級白鰭豚自然保護區,是白鰭豚遷地保護的最佳場所。這里過去是長江主航道,是白鰭豚的棲息地。1972年,長江自然裁彎取直后形成了現在的長江故道。故道長21公里,水面約3萬畝,水質潔凈,魚類資源豐富,不通航,人類活動少,沒有工業污染,完全適宜遷進數個白鰭豚群體進行保護和繁殖。國外專家甚至認為,這里是惟一適宜白鰭豚遷地保護的地方。專家建議國家加大投入,采用先進技術尋捕白鰭豚,力爭盡快捕獲幾頭白鰭豚放進天鵝洲故道保護區,以達到保護增殖和復壯種群目的。
記者近日在石首天鵝洲白鰭豚保護區了解到,故道內現在雖然沒有白鰭豚,但這里試養10多頭江豚已獲得成功。江豚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生活習性與白鰭豚基本相同。保護區管理處副主任肖四新介紹說,江豚于1992年遷進故道,它不但能在這里健康生活,還能正常交配繁殖。10年來,陸續遷進故道的10多頭江豚現已繁殖發展到20多頭。專家認為,江豚的成功為遷地保護白鰭豚提供了范例。
據悉,2002年秋季,國家農業部和中科院將啟動捕豚行動,爭取捕捉幾頭白鰭豚,以加大遷地保護和人工繁殖白鰭豚的力度。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2年07月15日第十一版)
| 我也說兩句 |
| 版權聲明: 1.依據《服務條款》,本網頁發布的原創作品,版權歸發布者(即注冊用戶)所有;本網頁發布的轉載作品,由發布者按照互聯網精神進行分享,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無商業獲利行為,無版權糾紛。 2.本網頁是第三方信息存儲空間,阿酷公司是網絡服務提供者,服務對象為注冊用戶。該項服務免費,阿酷公司不向注冊用戶收取任何費用。 名稱:阿酷(北京)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聯系人:李女士,QQ468780427 網絡地址:www.arkoo.com 3.本網頁參與各方的所有行為,完全遵守《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如有侵權行為,請權利人通知阿酷公司,阿酷公司將根據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刪除侵權作品。 |
 m.quanpro.cn
m.quanpro.cn